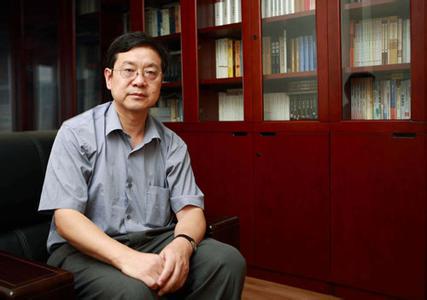
内容提示:始于西汉(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来得以维系和延续,故而体现出其典型的宗教之魂。本文将探究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交往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论及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并对这种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及意义加以分析、评价,由此明确指出宗教对于丝绸之路的价值,使人们能够以史洞今,为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关键词: 丝绸之路 宗教 中外文化交流
公元前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启程出使西域,拉开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历史戏剧的序幕。此后张骞两次西行,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通路,形成了相关国度“使者相望于道”的频仍来往,推动了欧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交流。
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为此,有必要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及其传入中国加以充分描述和认真分析。
一、丝绸之路上的佛教
张骞西游大月氏时始知印度之名、“始闻浮屠之教”,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遂从印度传入中国。其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西域传入佛教。此后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之说,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故建有白马寺。这一时期的西域乃佛教热地,不少佛教高僧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土流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亦应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在此前后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僧人还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其中不少人都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
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入后中国人西行求法之路,从而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形成呼应和互动。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而沿丝绸之路西往的中国僧人则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为始。此后,以陆行丝绸之路西游、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与此前后时期的西行者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经的玄奘(602-664年)和义净(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东归译经的感人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经乃是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之历史本源。
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佛教得以传入中国的“大乘”(大道),而这种佛教传播的来往亦使丝绸之路充满生机、显示灵性。“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一次,它进入中国后,很快便被中国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根开花,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二、丝绸之路上的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该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故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华故“始谓之天神”。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推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东传,并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一度盛行于西域,如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曾广为传播,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所推崇和推广。陈垣曾指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年),该教曾获得独尊之位,被其统治者带头奉祀,灵太后曾以“化光造物含气贞”之诗句赞颂该教,而其它祭祀崇拜却被废止。北齐、北周时也流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为该教之专指,而“胡天神”则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因该教兴盛而广建祆祠,统治者为之设立萨宝府和祀官,如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3]当时初传入中华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曾被误为来自波斯的该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经教”之称,随之亦以具有“日”、“火”蕴涵的“景教”来显示其光明之意。
丝绸之路既通西域,域外来华的“胡人”率先将琐罗亚斯德教传入,故管理祆祠的萨宝官职一般也由“胡人”担任。这些祆教徒主要来自粟特、波斯、以及今为撒马尔罕地区的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等,“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书·西域传》),其来华经商或定居者将此信仰亦带入中华,并逐渐影响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传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并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尤其在沿丝绸之路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该教影响颇大,信其教者包括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这一信仰的蛛丝马迹。[4]
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都曾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其在华兴盛于隋唐,后因伊斯兰教的强力传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对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产生了长久影响,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视之外,由其信仰礼仪习俗等演变发展的穆护歌、胡腾舞、胡旋舞、泼胡乞寒戏、拓壁舞筵也成为广为流传的文化遗产。
三、丝绸之路上的犹太教
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因为犹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踪迹所在亦是其犹太教到达之地。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但在丝绸之路所发现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则多为7世纪至14世纪之间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也有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记载,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5]而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乔寓定居之事实的,主要乃宋代开封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
犹太教在华始称“一赐乐业”教,为今“以色列”的同音异译,亦有人解释为此名乃根据明太祖的旨意,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态度。[6]而中国古代民间则将之称为“挑筋教”,其寺为“挑筋教礼拜寺”。而关于犹太人在华名称的记载及其演变,陈垣曾指出,“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元史语解》易术忽为珠赫。……术忽或称主吾,又称主鹘。”“至于一赐乐业之名,则起于明中叶。如德亚之名,则见于明末清初。犹太之名,则见于清道光以后。术忽之名见于元。《元史译文证补》又谓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7]
在华犹太教基本上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及其延伸路线来发展,到达开封的犹太人在宋代乃是从古波斯一带出发东进,沿途经过了西夏及西域其他国家,故有来自“西域”之说。但亦有人对犹太教来华持“天竺”之论,即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而来。记载开封犹太教的文献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记》称其“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经寺记》则说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为此有如下解释,“西域说就是波斯说,天竺说就是印度说。”[8]这两种说法都证明犹太教不是从其本土直接来华,而是经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在其沿线各国如中亚、印度等居住、生存,然后才辗转来到中国。这就使犹太教的来华传播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及宗教意识如此强大的犹太人及其犹太教却通过平缓的融合同化而在中华大地上消失,这已成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追溯、思考之谜。
四、丝绸之路上的景教
如前所述,景教之称本身就显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为其本原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是经历了其在波斯的嬗变才传入中华的,故景教在华初被误传为火祆教,“景”字本身亦与“火”字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称“波斯寺”。景教的传入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直接相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陈垣认为其初传乃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9]不过,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陆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朱谦之指出,“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10]应该说,景教在当时是活跃在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的一大宗教。
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唐会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毁佛灭教打压后,景教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而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扩展继续在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在蒙古人统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11]
宋元之际景教的发展不离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而且其影响的重点地区多在西域,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与发展曾给远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带来种种传闻和希望,如12世纪的欧洲曾流传东方有一位“长老约翰王”(或称“祭司王约翰”)信奉景教,曾率军远征波斯和米底等地与穆斯林交战,并攻克爱克巴塔那,只因底格里斯河涨水才阻止了其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一传说是欧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纪派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纪的西欧通过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来往及关联。
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里可温”的表述所取代,尽管人们对“也里可温”的解诂颇多,其共识为基督教之称则无异议。陈垣曾考证说,“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復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12]自唐以来论及基督教及其信徒有多种表述,如“景教”、“迭屑”(tersa)、“达娑”(Tarsa)等。“也里可温”在元朝指景教应无异议,元朝文献在论及也里可温时多提及聂斯脱利之名。不过,“也里可温”是否指元朝基督教的统称,尤其将元时入华的天主教也称为“也里可温”则尚无定论。陈垣在其《元也里可温教考》中大致承认“也里可温”包括天主教之说,他在引证时指出,“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教以礼东方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13]“谓也里可温为即天主教者,莫先于此。刘文淇道光间仪征人,阮元门下士。其说并非附会,较元史语解之解释为确切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14]“巴拉超士既谓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之Erkeun,是其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也。”[15]在该书第二章关于“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的内容中,陈垣也开章明义,直指西方教士之东来,并说,“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详。今巴黎文库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兰克王蒙文原书”。[16]显然,陈垣等研究者在此对景教与天主教并没有细分,而历史上两派却明显有别,如元朝东来的天主教在华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维诺就曾在其信函中宣称,“景教徒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远离基督教信仰。”他还进而指责“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17]实际上,元时镇江府大兴国寺碑文中论及的薛迷思贤按照穆尔的解释“即撒马尔罕”,[18]此为聂斯脱利派活跃的中亚地区,而非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欧。人们并没有清晰、明确地找到以“也里可温”来直述元代天主教的元朝汉语文献,而西文、蒙文文献只是经过翻译来间接地论及天主教在元朝的存在与发展。况且,汉语“天主教”这一表述本身乃明朝的用语,后人的翻译、转述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真实处境。因此,深化丝绸之路上景教发展演变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景教来华的具体路线、以及元朝景教与天主教的异同上进一步发掘。
五、丝绸之路上的摩尼教
摩尼教最迟亦于唐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史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教后于277年遇害,其门徒东逃,在3世纪末已将其教传入中亚。此后,在中亚、北非、印度等地都有了摩尼教的身影。
一般认为摩尼教于7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据中亚发现的文书残卷记载,摩尼教于675年传入中国。”[19]而“传统的看法认为,摩尼教是在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时才始入中国的。其根据是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三九的一段记载:‘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一看法,由于得到法国汉学家、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沙畹、伯希和(Pelliot),还有我国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肯定,因而广为人们所接受。”[20]但林悟殊指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要给摩尼教入华时间划一个准确的年代是困难的。但我们觉得,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21]
虽然丝绸之路因为冲突、战乱等政治原因而不时中断,却因这些经商者、传教者的执着、坚持而不断畅通。摩尼教传入中国后曾被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在民间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称。其传播扩大到西北、东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鲁番一带颇为兴盛,曾为当时外来宗教中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新疆、福建等地仍有许多摩尼教遗址、遗物的发现,见证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四通八达。731年前摩尼教在华可自由传道译经,此后遭唐玄宗禁止。8世纪时,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立高昌王国,以摩尼教为国教。由于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移居中原的回鹘人自768年被允许建寺传教,故在各地兴起摩尼寺院。840年回鹘亡国后摩尼教再度遭禁,但其流入民间称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宗教,直至15世纪在明朝的高压下才基本消亡。
六、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门、清真教、天方教等,在唐朝最初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当时的阿拉伯帝国被中国称为大食,“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始。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22]当时两国经济繁荣,商业往来频仍,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主要以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中国,故大多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卖出其运来的香料、象牙、药材、珠宝,带回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故海上丝绸之路亦为海上香料之路。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大多成为侨寓的“住唐”,并在华婚娶相通、娶妻生子,形成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信仰。
元朝时蒙古西征,将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这些人被元朝官方统称为“回回”,曾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壮观场景。蒙古人的西进以东西相连的陆地丝绸之路为主,他们促成了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推动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的发展。而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至16世纪,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
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则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亦使这些区域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发展有了明显提升。
七、丝绸之路上的天主教
天主教自元朝传入中国,其传教士的足迹覆盖了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并形成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深度交流。与经波斯来华传教的景教不同,天主教入华始于13世纪的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而这基本上也是围绕着丝绸之路才生动地展开了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自1221年以来蒙古人的西征使欧洲人大为震惊,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欧洲主教会议,决定派传教士作为使者东行,以争取蒙古大汗信教,由此开始蒙古与教廷的通使来往。
1245年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拉(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开了西方天主教东行的序幕,其在蒙都和林向定宗贵由呈交教宗致蒙古大汗书信,并得贵由复函而返。1247年,多明我会修士安山伦(Anselme de Lombardie)亦受遣东来。此后,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9年派多明我会修士龙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1253年派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来华。他们虽然没有达到其沟通和传教的目的,其对丝绸之路风土人情的精彩描述却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神奇而迷人的东方。125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东来经商,1266年在蒙古上都觐见蒙古大汗忽必烈,并受其之托回欧洲请教宗派学者东来,随之于1271年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来华复命。波罗一家久居中国,直至1291年才回返欧洲。马可·波罗后来口述《马可波罗游记》,传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佳话。
1289年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取道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东来,于1294年从印度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随后于1299年在大都建成教堂,遂为天主教来华开教第一人。天主教的东传成功丰富了中国的宗教生活,亦使中国有更多机会了解西方。不过,这段历史后被尘封,人们今天对元朝天主教知之甚微,学术界对也里可温与天主教的关系亦语焉不详,故需深入发掘,寻求突破。
丝绸之路经历的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交流之鼎盛乃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东传,其成就可圈可点、脍炙人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真正实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突破,天主教传教士由此使中西文化了解得以深化,中国人亦开始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语言的系统研究,而欧洲人也因此而获知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受到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影响。明清传教士在此过程中还实质性地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创立,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基本上引领着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其中尤以法国耶稣会士的贡献为著,他们在东学西传上的努力及成功,曾使西方一度流行法国人创建了欧洲的中国学之说。概括而言,法国耶稣会士当时的贡献也主要在于发现西来宗教在华传播的蛛丝马迹及其信仰精神的弘扬,以及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和对西方的影响,这大致体现在其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对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对《易经》的分析和索隐派思潮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古代编年史的梳理和与《圣经》编年史的比较等。[23]这些发掘和研究,使丝绸之路在连接东西方文化上的意义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并有力推动了其精神层面的比较与对话。
结语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保持,是东西文化在政治、经济交流方面的大事,而其中宗教的传播及其精神的沟通亦不可忽视。由于这些宗教传播者的东游与西行,丰富了丝绸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其地区面貌的变化发展,这尤其在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中国的传入,以及西域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嬗变上得到典型体现。这种发展演变作为文化遗产的积淀而保留下来,迄今仍可体会到其存在及影响。因此,我们今天在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必须关注其宗教文化的存在与交流,学会科学预见并理性驾驭其社会走向及影响
注释:
[1][19]沈济时:《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107、111页。
[2][3][9][22]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305、308、84、545页。
[4]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8月,第228-232页。
[5]《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97页。
[6]孔宪易:《开封一赐乐业教钩沉》,《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2期,第10、12页。
[7]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5页。
[8]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10]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61-62页。
[11]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页。
[12][13][14][15][16]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3、2-3、3、4、6页。
[17][18][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96、168-169页。
[20][2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46、60页。
[23]参见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71-225页。
(作者系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太湖文化论坛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5月4日文章;原文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感谢您的阅读!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读者的声音。若您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想法、疑问、建议或其他想与作者交流的内容,或愿意帮助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欢迎通过邮件(jidushibao@gmail.com)与我们分享。您的反馈不仅能帮助我们不断优化内容质量,也能让更多读者受益。我们会定期整理与回复大家的意见,优秀的建议还可能在后续更新中得到采纳。
反馈时,也请您具体指出是针对哪篇文章提出的意见与反馈。
期待与您保持互动,让内容在交流中不断完善。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