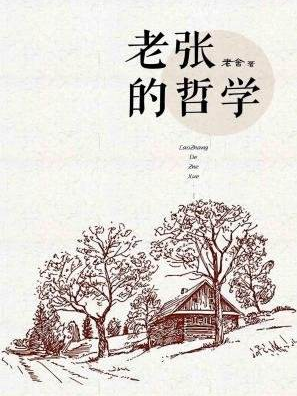
老舍写过很多脍炙人心的作品,但却没有专门论述女性的文章,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他对女性的漠视,反而他在小说里对底层女性这个苦难的群体给予了强烈的关注。
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女性一直没有太多的地位,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这道传统女性伦理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女性的身体和精神,让那些裹着小脚的女人,从此不得不依靠在男人的臂膀之下,充当着男人的玩物和财产。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反抗无门的女人们只能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在迷信和自怨自艾之中苟且偷生,其不幸固然值得可怜,但不争也有其可恨之因。从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为了女性走进教堂办女学开始,到大批留洋归来的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留学生为男女平等呐喊,女性的地位在中国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开始出现决定性地的转变。
这种转变既带来女性自主性的觉醒,也带来男性为女性的不幸遭遇而不平。从鲁迅的《阿Q正传》中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到祥林嫂的不幸人生;从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小翠,到老舍《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他们在努力用笔诉说着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告诉我们女性在那个时代生活的悲惨遭遇。
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他们开始审视束缚在女性身上的传统礼教,开始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不幸。
与“冰心在关注女性不幸的同时,也在基督教背景下塑造了理想的新女性”不同,老舍对女性的关注,主要是为她们的悲惨遭遇而投注笔墨。
在《老张的哲学》这部小说中,老舍描绘了李静这个底层女性,在封建礼教之下被卖的悲惨境遇。
李静从小是个孤儿,跟随姑母长大,姑母对李静来说是真的疼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看待。
李静的姑母是个极其普通的妇人,普通到足可以代表当时的中国女人形象:“李静的姑母有六十来岁的年纪,身体还很健壮。她的面貌,身材,服装,那哪一样也不比别人新奇。把她放在普通中国妇女里,叫你无从分别哪是她,哪是别人。你可以用普通中国妇人的一切形容她,或者也可以用她代表她们。”“她真爱李应和李静,她对她的兄弟——李应的叔父——真负责任看护李应们。她也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她是好妇人,好中国妇人!”因此,老舍对她的描述,其实也就是对当时中国女人的一个整体描述。
姑母生活在传统礼教中,受尽折磨和苦痛,但她对这种礼教却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自觉地维护,她出嫁之后做了人家媳妇,受尽婆婆的虐待,却认为这是做媳妇应该得到的,“我年青的时候,公公婆婆活着,鸡子?一根鸡毛也吃不着!我的肚子啊,永远空着多半截,就是盼着你叔父接我回娘家住几天,吃些东西。一吃就好!公公婆婆也不是对我不好,他们对儿媳妇不能不立规矩。”
姑母心地善良,对待李静是发自内心的爱,但对传统礼教又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因此,虽然她知道传统礼教的恶毒之处,但依然按照传统礼教来要求、教导李静。面对老张来买李静做妾的时候,姑母劝李静“好孩子,人生大事,是该如此的!”这就是中国女人命运的循环——在传统礼教把自己吃掉之后,还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它的口中。
为了还掉李静叔父的债务,叔父把李静卖给了老张,虽然李静和邻居王德青梅竹马,私定终身,但在孝道面前,李静选择了嫁给老张做妾,牺牲自己的爱情。姑母为了防备王德从中作梗,一刻也不离李静的身,并力劝王德的父母把王德赶到乡下或者娶个老婆。姑母俨然成了维护孝道的卫士。
自己深受礼教之苦的姑母,在李静出嫁的前一天晚上,还要敦敦教导李静如何守好妇道,“赵姑母的眼泪不从一处流起,从半夜到现在,已经哭湿十几条小手巾。嘱咐李静怎样伺候丈夫,怎样服从丈夫的话,怎样管理家务,……顺着她那部‘妈妈百科大全书’从头至尾的传授给李静,李静话也不说,只用力睁自己的眼睛,好象要看什么而看不清楚似的。”无助的李静,只能任礼教宰割。
在姑母看来,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做玩物的,男人给个吃穿用度就应该满足了,“这是正事,作姑母的能有心害你吗!有吃有穿,就是你的造化。他老一点,老的可懂的心疼姑娘不是!嫁个年青的楞小子,一天打骂到晚,姑母不能看着你受那个罪!”在礼教之下,绝望的女人只要能活着就应该满足,礼教之下,女人只能像个动物一样,为自己寻一个不打骂的主子。
老舍在通过姑母和李静,告诉我们女人的遭遇正是在礼教中如此绝望地循环的。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绘了小福子这个女性的悲惨,她即充当男人的玩物,也卖淫充当父亲喝酒的钱袋子。
父亲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以两百块钱卖给了一个军官,父亲用卖女儿的钱买了车,为家人和自己置办了新衣服,“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
而买小福子的军官既不是买她做妻,也不是买她做妾,而是买她既当仆人又当性伴侣的玩物,“买小福子的人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么?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等到军官开差离开之后,小福子便被抛弃了,还不得不卖掉床板和椅子,付掉军官所欠的房租。回到家里的小福子面对的是母亲被父亲打死之后的破败家庭,为了养活弟弟,她不得不卖淫,但是即使如此,父亲还颠三倒四地找她,一面骂她是个淫妇让自己丢了颜面,一面又找她要钱喝酒。
《四世同堂》里的韵梅全部的人生价值就在于成全传统礼教,对上伺候公婆,忍耐公婆的打骂,对下照顾孩子,伺候丈夫,却唯独没有考虑的是自己,这恰如法利赛人的律法,一切都要为了律法,人自身是没有价值的。《正红旗下》的大姐,更像婆家养的宠物,连回趟娘家的权力都没有。
老舍自己的立足点显然是西方文化中的男女平等,只有如此才能描述中国奴隶地位的女性。老舍把自己的笔墨倾注于他们,关注平民女性的悲惨遭遇,这源于他内心对女性悲惨地位的不平。
感谢您的阅读!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读者的声音。若您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想法、疑问、建议或其他想与作者交流的内容,或愿意帮助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欢迎通过邮件(jidushibao@gmail.com)与我们分享。您的反馈不仅能帮助我们不断优化内容质量,也能让更多读者受益。我们会定期整理与回复大家的意见,优秀的建议还可能在后续更新中得到采纳。
反馈时,也请您具体指出是针对哪篇文章提出的意见与反馈。
期待与您保持互动,让内容在交流中不断完善。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



